“史家注史”,探索古代正史现代化的新形式——访《今注本二十四史》执行总编纂孙晓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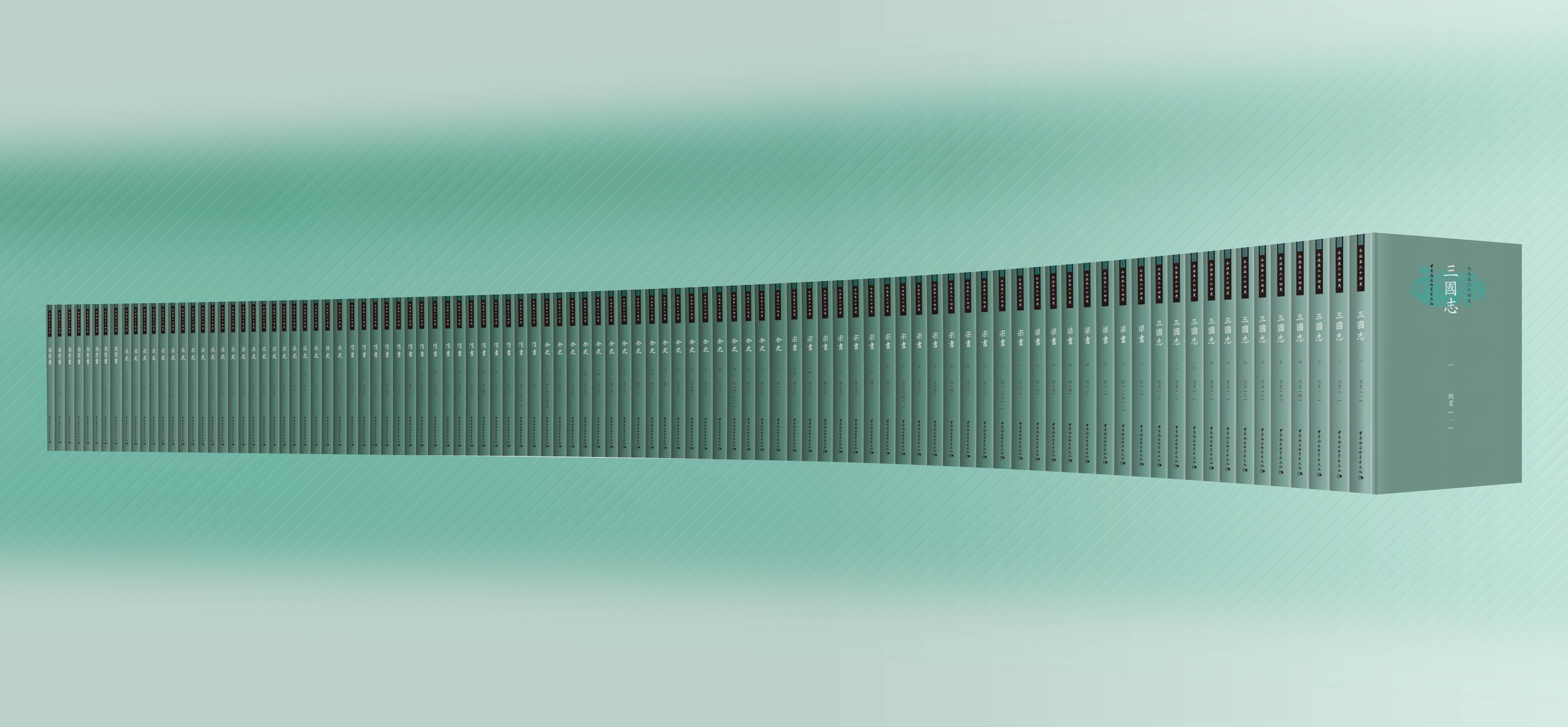
《今注本二十四史》项目启动于20世纪90年代,历经20余年,首批七种《三国志》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梁书》《北史》《隋书》《金史》近日出版,堪称史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件盛事。本报记者特别采访了该项目执行总编纂孙晓研究员,请他谈谈图书背后的故事。

孙晓,1963年9月生,河南正阳人。1983年参加工作,198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获硕士学位后留所工作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史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秦汉史与经学研究。主要成果:《中国婚姻小史》《心斋问学集》《两汉社会与经学》等;合著《阳刚与阴柔的变奏》《中国经济通史·秦汉经济卷》《阅藏知津》;主编《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丛书》(5种)、《掌故大辞典》等。
记者:作为《今注本二十四史》的执行总编纂,请您分享一下《今注本二十四史》立项背后的机缘故事。项目启动于20世纪90年代, 现在回头来看二十多年的编纂工作,您有怎样的体会?现在最新的项目进度是怎样的?
孙晓:我忝列执行总编纂,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是一种荣誉。总编纂张政烺先生和另一位执行总编纂赖长杨先生都去世了,截至今日, 先后有20位主编、顾问去世。现在我除了感觉孤独以外,更是感到责任的沉重。古籍整理无法做到尽善尽美,再仔细认真,也会有错误。所以从事这项工作的学人常说:古籍整理,如同秋风扫落叶,风来了,叶又飘一地。我怕秋风,可现在就是秋天了,我们的书出版了。我深深地知道,我们的书,如果得到一点赞许,荣誉是各史主编与作者的;如果出了问题,责任肯定是我的,无人能分担这份沉重。
开展《今注本二十四史》项目是我的主意。20世纪80年代初,在我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读研的时候,我的导师之一李祖德先生让我注意阅读明清人研究“前四史”的成果,看看能否摘录下来,以后可以编一个资料集。“前四史”即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,这些是“二十四史”仅有的带有注释的史籍,但都是唐以前人的旧注。唐以后学人心得笔记均散见于各文集中。我当时就有个想法,若是把这些研究成果,会同当代考古文物的成果,与正史的文本缀合一起,以后我们读史将会很方便。20世纪90年代初,有一次我与赖长杨先生闲聊谈到这个想法,他非常兴奋,说这是完成古代正史现代化形式的大事,立志要与我一起把这件事做起来。他治史学史,对这个项目意义的理解更深。于是我们便撰写了编纂计划、凡例与样稿。
做了这些前期准备后,我们开始联系出版社。兜兜转转在几家出版单位游荡几圈后,终于在我的好友中国社科院科研局朱渊寿先生介绍下,认识了中华文化促进会的王石先生。王石先生是一位有理想的读书人,慧眼独具,对这个项目的价值有很深的理解。他把这个项目引进到促进会,并获得文化部的立项批复。1994年10月,本项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开笔典礼。
从开笔到今天,过去了二十六年,其中甘苦,难以详述。这些年,经费一直十分拮据,断粮是常态。2018年,还是王石先生的苦心与坚韧,感动了深圳华侨城集团,在华侨城集团段先念先生支持下,本项目的经费得到了保证,编纂工作开始步入正轨。我们计划今年推出13部,明年推出5部,2023年完成全部编纂出版工作。
记者:“史家注史”是《今注本二十四史》的重要特色,在每一史的具体负责人的选择上, 标准是怎样的?核心人员有哪些?大概有多少人参与了这项工程呢?
孙晓:“史家注史”是我们编纂工作一直倡导并践行的原则。我们要求历史学者而不是文献学者,来担任各史的主编,并由历史学者参与本书的注释。古人说,“文史不分家”,这只是大致的看法,其实还是分的。汉代有“两司马”,即司马迁与司马相如,如果让司马相如去写《史记》,司马迁去写汉赋,会成什么样子?现代的学科分类,文献专业归中文系。文献学者注史侧重的是版本、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等问题,历史学者则关注史事的疏通与正误。举一个例子,古史中常有“亡命之徒”,我们一般理解“亡命”就是“不要命”,这是不对的。文献学者或根据古人的注疏,把“命”解释为“户籍”,“亡命”就是“没有户籍之人”,这是不全面的。历史学者则会根据出土简帛与传统史料的印证,进一步解释,“亡命”是指“已确定罪名而逃跑的人”。这里不是说历史学比文献学高明,只是学术旨归不同而已。文献学者在版本、文字等方面的高度也是历史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。
“史家注史”作为我们编纂工作的指南,也彰显了这个著作体系的特色。应该说,近代以来,古籍整理、为典籍作注疏大都是文献学者的工作,现在,历史学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,会凸显自己学科的优长,可以在史实疏通、制度流变、名物考证等方面多做一些工作。我们各史主编、作者基本来自历史专业,全国三十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300余名学人先后参加了这个项目,核心人员都是在各断代史上学有所成的知名专家。
记者:《今注本二十四史》首批7种——《三国志》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梁书》《北史》《隋书》《金史》近日面世,成为本年度史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件盛事。在公共馆藏和个人收藏方面,您对这批书有怎样的预判?这批图书会为哪类读者带来助益呢?
孙晓:司马迁说过:“有国者,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。”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较,中华文明绵延不绝、从未间断,这多得益于我们史学记述体系的完整,修史是每个朝代确定自己的位置的基础工作。只有学习历史、研究历史,才能知道我们的今天来自于我们的昨天。一个没有悠久历史的民族,是容易健忘的民族, 不会有光明的未来。
犹太民族是最有智慧的民族之一,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,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离散聚合,甚至失去家园,四海飘零。但犹太民族至今还健在,未被其他民族同化,是因为他们一直传承与笃信自己民族的经典《旧约》与《塔木德》,犹太人信仰来自《旧约》,智慧源于《塔木德》,这两部书是犹太人的精神纽带。中国的史书也有类似价值。
我认为《今注本二十四史》首批7种,作为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古代正史的现代化形式版本,会成为公共图书馆必藏的图书。此外,我希望这些著作,也为个人所收藏,因为它们不仅适宜阅读,而且版本精致,有收藏价值。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一个家庭的书架摆放一部二十四史,比供奉一个神龛,所带来的福泽要多得多。
记者:“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”,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如是说。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内涵的?您觉得出版社、图书馆为此可以做哪些工作?
孙晓:我们说过,编纂《今注本二十四史》,目的就是完成这部古籍的现代化形式。我不太赞成把古籍翻译成白话,理由是翻译不可能准确传达文章的内涵,也会破坏古文的意蕴,更重要的是译者会用自己的理解代替读者的理解,使读者丧失掉学习的机会。而今注则是一个较好的形式,即注释者把自己的心得与读者一起分享,一起徜徉在古人搭建的历史空间。
完成古籍的现代化形式是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基础。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,我们便可以在上面盖房子了。
我觉得出版社不能只满足于出版文本类书籍,应该注意保护与开发所出版书籍的IP,IP的能量是无限的,这也许应该是出版社未来发展的方向。图书馆更应该根据自己所在地的历史文化资源,开发与保护和本地IP资源有关的IP库,为当地的文化建设服务。《今注本二十四史》中许多人物、事件、典章等都是IP,地方特色也十分鲜明。
记者:“学史使人明智”,在引导青少年提高历史文化素养这一点上,除了通用的“死记硬背”知识点以外,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?
孙晓:是的,“学史使人明智”。我的理解是,学史不能靠记忆。当然,死记硬背一些章句,也是有用的,起码可以用来谈恋爱。学史明智指的是要学会用历史的方式思考问题, 即理解一个问题时要关注其产生的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,这样才会不偏颇。比如,美国现在“Black lives matter”的社会动乱,很多人都认为是“左右”矛盾,即种族矛盾;其实若用历史的思维理解,即考虑美国近百年财富分配的变化,很容易发现这不是“左右”矛盾,是上下矛盾,即贫富矛盾。只不过是美国上层精英,巧妙地用“左右”矛盾来掩盖上下矛盾罢了。“左右”矛盾只是动荡,可以控制;但上下矛盾,搞不好就会天翻地覆。
记者:在您的研究生涯中,图书、图书馆各扮演怎样的角色?您一般是从哪些媒体(包括传统媒体和移动APP)上关注历史文化领域的动态的?
孙晓:我非常喜爱书。小时候,我父亲的藏书有很多,我读了不少。记得上小学时,有一段最幸福的读书时光。那是在“文革”时期,我们地区很多旧书被没收了,堆在汉代名士黄叔度的墓后边一个大屋子里。我经常钻到大屋里,爬上书堆,斜倚着木格子窗户,静静地读书。中学的时候,父亲把收藏的“文革”前的《历史研究》送给我,我很爱读,还把这些杂志拆开,分类再装订起来。我也酷爱买书,来北京上学时,几乎每周都去琉璃厂或中国书店,买的书太多,以至于后来要租地下室来存放。但我买书,只求有用,不太讲究版本,这颇有些遗憾。当时和我一起买书的朋友,他们喜爱买好的版本,当时几块钱的书,现在他们拍卖两部,就可以买一套房子。
图书馆是我经常去的地方。20世纪80年代初,我的第一篇历史论文就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,这篇论文还入选了河南省第一届大学生论文宣讲会。1987年,我的第一本书出版,这本书也是在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完成的。图书馆是这个世界最安静的角落,也是最自由的天地。
说实话,我不太习惯在网上读书,但我知道,电子书与在线阅读是未来,不可能改变。对历史文化领域的动态,我习惯通过看一些杂志或图书来了解。我不爱通过手机APP和微信公众号看信息,我认为那都是别人咀嚼过的食物,虽然好消化,但毕竟没有什么营养了。
记者:请您给读者推荐三本历史类通识读物,并简要说明理由。
孙晓:我推荐《中国历史极简本》,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,言简意赅,灼见时出;《中国通史》,由华夏出版社出版,平实中肯,论述精辟;《中国通史简编》,由人民出版社出版,典雅方正,规范认真。
本文刊登于《图书馆报》第523期

相关资讯
more- 舒伟:“童话”被矮化,童话文学理论建设迫在眉睫
- 剑桥中国史
- 第六批《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》 征稿函
- 科研经费管理 少检查多服务
- 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
-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6年招聘启事
-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公开招聘启事
-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习生招聘公告
-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关于招募社科书评人的通知
- 两部经典国学读本出版
- 分享生命奇迹的励志奇书
- 阅读中国 献礼华诞
- 《中央苏区研究丛书》首发式在南昌举行
- 中国外交甲子纪事
- 《剑桥中国史》出版史
- 《通往奴役之路》走上畅销路
- 《马洪文集》出版发行仪式在京举行
- 十二卷本《马洪文集》出版发行
- 《任继愈宗教论集》出版 追思先生治学风范
- 百年论先贤 贡院话翰林